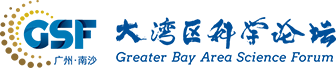去年6月,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简称《南沙方案》),要求高水平建设南沙科学城。今年2月,省政府批复了南沙科学城总体发展规划,南沙科技创新事业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在刚刚过去的2023大湾区科学论坛南沙科学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分论坛上,南沙科学城发展蓝图的谋划者、起草者穆荣平先生以《创新促进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南沙科学城与城市创新基因再造》为题做主题报告,现将演讲原文摘编如下。
非常高兴参加大湾区科学论坛, 今天这个题目叫“创新促进发展、科技引领未来”,源自于20年前中国科学院在上一轮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期间给中央一个报告的名字,通俗讲“立足当前”是抓发展的问题,“着眼长远”讲的是科技的问题,科学城从一开始建设时是“着眼长远”又和当前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讲南沙科学城规划和城市创新基因再造。
改革开放那么多年,通过引进国外的生产能力、使用技术,慢慢地改进技术,所以我们的创新能力是逐步演化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今天时间关系,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因为南沙科学城规划已经得到批复,现在在落实,我想要把握时代脉搏,最近我们经常要讲的三个词组合在一起:一是创新驱动,二是数字转型,三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城总得来讲要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因此我说它是已成为世界潮流。
第二,南沙科学城肩负着厚植城市创新基因历史使命。
第三,愿景引领科学城,驱动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创新驱动+数字转型+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潮流
我记得2004年美国出了一个报告叫《创新美国》,导致美国一个创新竞争力法案;2005年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搞“创新国家”,日本有了一个“创新国家”,安倍上台后就变成“创新2025”,又有面向“创新的欧洲”,英国也有个“国家创新报告”,印度也有。因此,可以看到20年前左右创新在各个国家的创新议程里已经占据了非常突出重要的作用,我们科学院以前的报告也提到,科学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决定性因素,这些在20多年前就有了。另外,数字技术的演化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网络到上世纪末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再到进入本世纪2001年的日本E-Japan、U-Japan、I-japan以及到欧盟的类似报告,包括美国的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从1998年浮现,到2000年就有了,所以“数字经济”也讲了20年,在过去20多年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规律性认识,我们经历了从电子化到信息化,再到数字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在这个演化过程最近比较火热的东西,一是前几年的元宇宙,还没有搞清楚又来了一个Chat GPT,IT行业是喜欢造些新概念,但更重要是引发我们去思考未来的可能性,技术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断给人赋能的,它和科学不一样,这个赋能带来的是多方面的转变。日本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是社会5.0,兼容了德国提出的工业4.0,即把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生活、环境各个领域,所以每年都有新进展,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把联合国17类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子目标都镶嵌在大的、系统的数字转型里面去。一句话,创新驱动、数字转型改变世界是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从范式转变角度来说,即改变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发展、环境发展、社会服务发展,文化发展的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变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意味着很多新机遇。我们国家已经把创新驱动数字转型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数字中国的三个方面,今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布局》,增加了数字文化、数字生态文明,这充分表明数字转型会越来越深入,拓展的面会越来越宽,它会改变我们这个时代,因此各个国家都在做,我们从过去浅层次的互联网+,到未来是+互联网,网络技术是各行各业必须要用到的东西,恢复互联网高速的基本功能,我们认为这是个潮流。
厚植城市创新基因是南沙科学城第一使命
在这样的潮流下南沙科学城第一个使命是厚植城市创新基因,过去我们讲“创新”,从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有大量的军工技术是需要找到市场的出口,所以军转民开始,在政策议程里就把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引入到政策议程里,所以有了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变,重点是要找到其市场价值。那么多年我们可以发现有个轮回:市场价值的本源,即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还是需要公共的投入,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创新从五个方面来定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能力强的和能力弱的企业间的差别,最主要是价值创造,比如科学价值创造,技术价值创造,每类主体有不同的定位,所以二十大报告里也提到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和布局,这样对科学城来讲是需要去思考的,中国科学院也在思考在大湾区,特别是在南沙科学城的布局和定位的优化问题。我们把这五大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叫创新绩效,我们曾经用两个指数来测试,一是创新发展指数,二是发展能力指数。因为创新作用在发展的结果,即创新发展的水平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另外创新作为一种力作用在发展上,这个力的大小也是需要关注的,所以是能力指数和发展指数两个共同来看创新绩效。因此我们在科学城建设中是贡献了创新能力建设,当然能力作用在发展上面,还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能力在提升,未来可期;能力在下降,未来会有问题。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用技术落地、建设生产系统,引进世界500强都是以制造业工厂为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时代,传统工厂发展方式很难引领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原有的区域经济基础上要打造区域的创新发展的引擎,而这个引擎的核心就是科学城。
愿景引领科学城驱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做南沙科学城研究时,回顾了世界主要科学城的发展历史,早期的科学城是以大装置为主,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过去十多年,在科学城周边聚集了一批创新创业的园区,这可能也是个国际大趋势。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城跟原来最早50年代、60年代讲的科学城是有所区别的,在中国3+4,像北京、上海、大湾区,或者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大湾区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通常是以大科学时代里的大装置建设为主要的任务,但是它不能局限在大装置,这也是科学城规划时要考虑到的。在南沙科学城规划里面提到要聚焦四个愿景:创新全球化、制造智能化、服务数字化、环境绿色化。这里面几个方面,包括全球化,在数字赋能的条件下跟过去的全球化应该也有所不同,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全面创新改革为动力,营造成就全球天下英才创新创业事业梦想的制度文化环境,建设大装置集群和科学人才队伍。南沙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全球海洋科学与工程的创新中心,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科学院的南海所及广州地调局,包括天然气水合物及相关的地质研究力量,我们要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产业策源地。
在能力建设方面,大科学设施在最内核,周边是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这种战略科技力量,之后是创新创业,再往后就是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再往后是战略创新产业集群,这恰恰可以看到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态式,最内核部分就是科学城需要重点做的事情。从科学技术价值创造,到经济社会价值创造要实现统筹安排,中间有个特别重要环节是创新创业,基于创新的创业所衍生出来的企业,自身就有技术创新的链条,因为跟技术源之间有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可以把战略科技力量的能力,能够跟产业间建立很好的创新生态。同时,科学城不仅是南沙的科学城,同时是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全球协同圈,要注重开放合作。在产业创新发展政策、社会创新发展政策,在前端科学和技术价值创造等方面,跟中央可以合作,有所分工侧重。最后总结一句,创新驱动、数字转型、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愿景引领能力建设、政策保障是新时代科学城必须思考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与学科建设、技术领域,战略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相互支撑迭代与内在驱动力。充分认识科学城建设肩负着城市创新基因再造的新使命,充分认识数字转型引发的科学研究一系列范式转变,这些转变带来的战略机遇我们要营造创新者友好的制度文化环境,从吸引人才,向成就天下英才转变,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子。
附件: